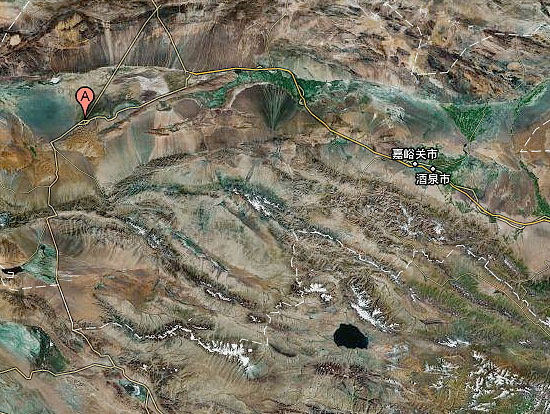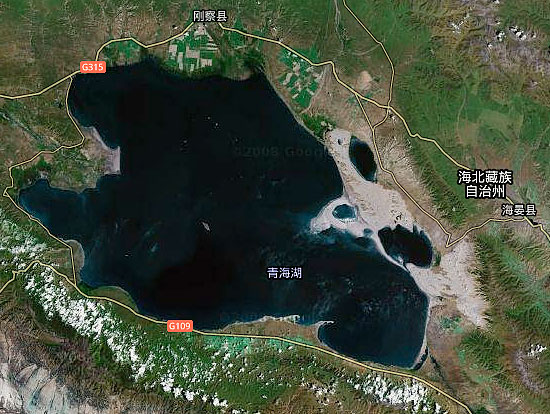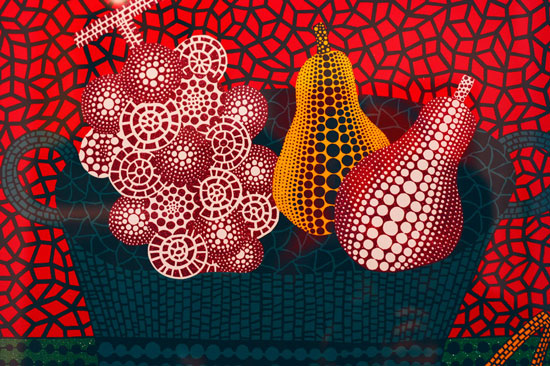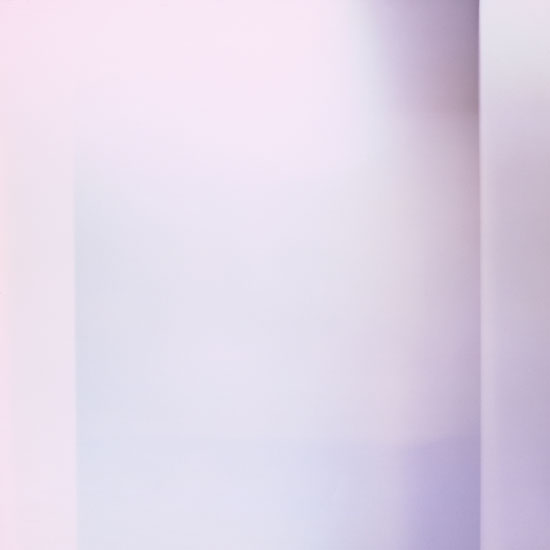▲▲
7月 29, 2010
7月 18, 2010
日记
看到2010最美的一次日出
在凌晨4点半的时候。
这让我意识到几乎已经整年多没看过日出了。
好好的站在一个地方看。
我在十字路口中间站了会儿,
天空从乌兰快速变成粉红。
温柔的不像话,
活生生走在伤口上。
四处都有鸟叫声,
听也没有听过的鸟叫声,
有的很近,有的很远。
尽量把脑袋空白,
想拍照,但手很软。
6月 27, 2010
蚊子
1点半了
关了灯,一片黑暗
一只蚊子飞过耳边
我试着不去理它
房间关着窗,闷闷的
15分钟后它又过来了
还带着得意的哼哼声
妈的~开了灯
它忽隐忽现的招摇
太高,打不到
又关了灯
各式各样的幻影,想法
一略而过,又浸在馄饨面里…
然而它又来了,
在2点半,3点,4点,五点,准点来报时
五点那次,彻底怒了
已经被咬了三只包
啪啪啪啪,开了房间的四盏灯
狗娘养的就停在白色天花板上
肚子红红圆圆的
身上所有的包都在笑我
我沉默的把被子抱走
再小心的把椅子垒在床上
赤着脚,站在椅子上
看着它
一只丑蚊子,脚上的花纹都没有
长着蹩脚的灰翅膀
吃饱了,脚都不动一下
我憋着气,默默的摊开手掌
向上
压碎了,再碾了一下
安心的躺下来,睡着了
它居然飞在我梦里
哼哼唧唧的
我在梦中想象它的样子
象相机慢慢聚焦,慢慢清晰
一只不起眼的灰蚊子
在梦中我摊开了想象的手掌
狠狠的拍过去,
“啪”
窗外已经蒙蒙亮了
6月 23, 2010
6月 22, 2010
5月 23, 2010
5月 16, 2010
5月 9, 2010
5月 4, 2010
5月 2, 2010
奢侈
已经连续睡了两天,
窗外是上海少见的好天气,
阳光穿过树叶,满眼油润翠亮,
恍惚间又是一个夏天的光景。
但是没有兴趣起床,
压在枕头下,世界黑而静,
想起小学暑假时候去数学老师家补课,
老座钟每过半个小时就悠悠的敲一下,
我就一边想着那钟声,一边又稳稳的烂进梦里。
4月 18, 2010
4月 4, 2010
耳朵
最近右边耳朵一直在说话,
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劈里啪啦
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劈里啪啦
说的小声又坚决
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
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劈里啪啦
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劈里啪啦
甚至夜深人静起来尿尿的时候,
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劈里啪啦
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劈里啪啦
我仔细的掏了耳朵,没有用。
似乎它忍耐了好久,这次真的要和我摊牌说分手。
所以,在这首和下一首的间隔里,
在每段谈话的沉默中,
在入睡时,魂灵头飘荡坠落前,
它都努力在屁话。
耳朵突然变成了独立生命体,
说着我所不理解的语言,
想像着《寄生兽》或者《神经》(圣经)。
也许它所说的很重要,呢?
也许是什么鬼上帝在指导工作,或者什么鬼祖先在召唤纸钱?
2012?九点一刻在莱福士的下水道有外星飞船?
窪塚洋介会在女厕所第2间出现?
虽然满可笑的,但其实我还是很仔细去听它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真的只是劈~里~啪~啦~ 罢了。
两天后,我已经开始习惯它的屁话,
660下,从小区走到家门口,
10下,下首歌的前奏就会响起,
可以听到它的时候,常常是一个人的时候,
我想耳朵它比较害羞,人多的时候就不好意思抱怨了。
然而昨天到今天,睡了快36个小时以后,
它突然沉默了,不论我怎么屏气凝神,
怎么用心发问,它都没有再说话了。
好像耳朵已经死掉了那样。
我好像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压死自己小猪的老母猪一样
有-点-伤-心
3月 21, 2010
Finally
终于把该看的,看掉了。
阿凡达很糟糕,还不如平时做梦时候看到的景象。
因为电影还早,下午就无聊喝喝咖啡,翻翻刚买的杂志,
看到了里面的一句话,叫”原谅他人即自我疗伤。”
说的是个心理学博士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着一个关于”宽恕”的课题。
他把那些久久不能释怀的情感比喻成在空中盘旋的飞机,
空消耗能源,却不能降落。
他说”这些愤怒的飞机慢慢积累着压力,最后的结局通常是坠毁。”
除非你可以宽恕, “宽恕则是着陆后那一刹那的平静。”
很诗意的比喻。
我想像着现在天空上如乌云一般,遮天蔽日也不能落地的飞机。
然后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一架的栽在地平线上。
哈哈。